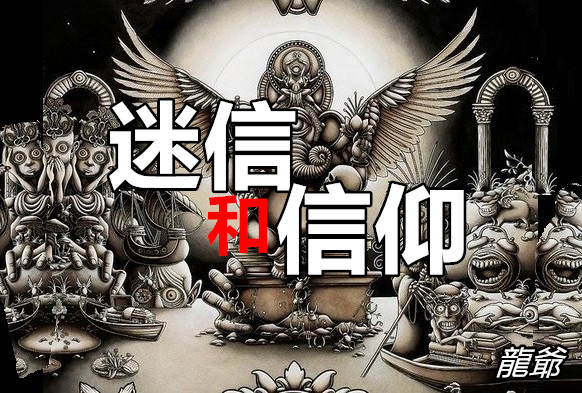《大乘佛教的產生與奧義書的關係》
(先說明這篇文章確實有點長,而且沒啥圖片,非打起精神殺死些腦細胞不可,否則你不可能讀完。)
在印度宗教的哲學思想中,最大最正統的要算是「吠檀多」或稱「吠陀」,而最大的異端卻是「佛家」,二者的相互關係影響了印度思想史。
大多數印度思想史家認為,「佛教」的基本世界觀乃是從「吠陀與奧義書」思想發展而來,實際上 釋迦牟尼 本人在出家初期的確受到《奧義書》思想重大的影響,比如業力,因果,三世輪回,苦,解脫,四禪八定,六道眾生,諸天等等。
但「佛教」的核心部分乃是在宣揚形而上的本體論,籍禪修,苦行等方式,期待小我(本具自性)與本有的真常大我、梵我(如來藏)合二為一而脫離三世輪回之苦,回歸清淨的本性。
而「原始佛家」的核心思想是說明 釋迦牟尼 因為洞見人體「六處入處」因為「根境識」的關係導致「五蘊」生起情緒煩惱痛苦,續而流轉生死的真相,並以此「緣生法」正見理念修持「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出生死煩惱。
一直到了「根本佛教」時期,因為《阿毗達摩》的出現導致變更法理,才從「佛家」逐漸演變成「佛教」,提倡「三世實有」說,宣導「無常,苦,空,無我」等思想,企圖通過修習「安那般那」和「毗婆室那」禪法斷除生死煩惱解脫的理念。
佛滅數百年後,《奧義書》的思想日益深入的滲透到「佛教」中,使「佛教」的思想產生更大的演變。從「部派佛教」的「三世實有說」,到「大乘佛教」絕對唯一的「真如法性」,最後於西元五世紀後產生的「如來藏佛教」描述一切眾生本具清淨自性,真常唯心的內容,使到「佛教」成為了佛梵雜糅的產物,逐漸被《奧義書》的思想所同化。
「大乘佛教」是西元前二世紀在古印度出現的新思想,它的特點包括了:強調悲願,入世利他,菩薩信仰,神通示現,他力庇護,梵化的佛性涅槃論,絕對的佛陀觀,超經驗的形而上學等。
學術界充分意識到,這樣的思想是與「原始佛家」思想是完全隔裂的,而另一方面又體現出與《奧義書》中形而上的思想完全一致的特點,如:不二、平等、如夢如幻、假有、二諦、無分別、唯心等,這在佛陀時代的「佛家」是絕對找不到根源的。
「大乘佛教」的產生絕對不是一種單一的運動,而是相互鬆散聯繫的思想趨勢的整合結果。1.禪觀的新思想,2.菩薩行的開拓,3.淨土信仰主義的強化,4.脫離「部派佛教三世實有論」,妄想恢復「吠陀本旨」的衝動,而這些新興的思想無論從個別還是整體上看,都反映出《奧義書》思想對「大乘佛教」的影響。
【一 .禪觀的發展與大乘諸派 】
「大乘般若」和「瑜伽」思想的產生都離不開禪觀的發展,這一點在大乘經典中可以得到證實。如現存最早的《八千頌般若》中說六百萬三昧門,謂得是諸三昧已,了達般若波羅蜜,住阿毗跋致地,《小品般若經》卷十明確指出禪法的三昧是般若的根源。
從邏輯上說,在印度沙門文化的包圍下,《奧義書》中「真常唯心」的思想通過禪觀管道,被皈依佛教後的外道大量的引進佛教,在沒有「經部長老」審核監督的時代,這是很自然的事。
般若的思想可能來至於不屬正統僧團的遊方吠陀苦行僧,相對於部派僧伽的獨立性,他們的禪觀內容更容易接受新的啟示,包括來至於《奧義書》的啟示。《般若經》暗示了「大乘禪觀三昧」與《奧義書》形而上學的一致性。
如:1.離幻 、空花、如鏡像三昧,2.無礙解脫、性常默然、不壞、光明、離垢清淨三昧,3.無差別見、諸法不異、離一切見、離一切相三昧,4.諸法不可得、離一切著、破諸法無明、離塵垢、離一切暗三昧等等。
這些禪觀的思想內容,在「原始佛家」、「根本佛家」、「部派佛教」中是絕對沒有的,但卻與《奧義書》中的梵、真我、如來藏、空性、第一義的世界觀有著本質上的一致性。比如「離幻三昧」等,就與《奧義書》觀證世界為幻、唯梵(常住真性)獨真完全一致。
如「無礙解脫三昧」,則於《奧義書》中的梵(常住真性)離言詮、離相、解脫、恒常、光明、安隱、清淨無染毫無本質上的區別。如「無差別見三昧」,則於《奧義書》中觀想梵我平等一味、無見、無相、無差別完全一致。如「不可得三昧」,與《奧義書》中常住本性乃離諸名色、不可知、不可得、不可著如出一撤。
《奧義書》中這些禪觀思想的出現更早於佛家,而「原始佛家」並無這些內容,因而可以肯定,般若三昧的第一義諦,空性等思想,完全是受到《奧義書》中常住真性的影響,或者說,「大乘般若」的思想完全是在《奧義書》的啟示下產生出來的新思想。
另外,於西元四世紀出現的「大乘瑜伽行派」也是受《奧義書》的思想啟示演變而來的,在早期的「部派佛教」時期,就有不事議論,專修瑜伽的瑜伽師,後者正是由於導入「唯識性」的禪觀理念而形成了「瑜伽行派」。
雖然在《阿含經》中也有一些隨順「識本論」的內容,但是屬於極其偶然的。很難想像,數百年後會演變成一個完全獨立的「大乘學派」。
「識本論」乃是《奧義書》的主流思想 ,而《阿含經》中「識本論」實際上也源於此,且《奧義書》要求禪修者觀「名色」(五蘊)唯是識,這與大乘的唯識觀一致。
因此可以確定,佛滅後,有些皈依佛教的外道,把《奧義書》的禪觀方法融入「佛教」,從而形成諸法唯識的觀法,但同時,他們試圖從《阿含經》中尋找根據,最終導致了「瑜伽行派」的產生。
正是《吠陀奧義書》中形而上的哲學思想論述《阿毗達摩》滲透進「佛家」,這才是引起後來「佛教」思想大變革的真正原因。當由此形成的新思想被表達出來,就形成了「大乘初期」的「般若」和中期的「唯識」思想及「中觀」思想。所以,不管是「般若」思想,還是「瑜伽」的思想,都表現為對《奧義書》形而上學的回歸。
「部派佛教」時期的教義宣揚的是「緣起」「無我,無常,苦空,不淨」,而到了後來的「大乘」各派時期,處處在宣揚「真常大我」,「常,樂,我,淨」。
【二. 大乘菩薩道的形成】
佛滅百餘年後的「部派佛教」中,因信徒的緬懷,從而出現了《本生》、《譬喻》.《因緣》、《方廣》等經典,還有後人編撰的傳記文學塑造偶像,因此「菩薩」的觀念逐漸的形成。
「菩薩」最早是指「原始佛家」時期對沙門的佈施供養者,到後來的「大乘經典」中,凡是發誓度眾生的人皆被指為「菩薩」,排行在「四果阿拉漢」之上。然而盛行於「南傳上座部」的「菩薩道」思想則又完全有別於西元一世紀出現的「大乘菩薩道」理念,顯然它們都是由後人編撰發明而成。
「大乘菩薩道」又稱為「大乘佛教」,它是以大慈大悲,大願大行為主要特徵,它的產生自然是以菩薩思想為重要資源。然而,從「原始佛家」的樸實無華,逐漸演變成很多佛菩薩,出於大悲系統拯救的行為。從「原始佛家」宣導「解脫」為最的理念,轉變為「大乘菩薩」提倡慈悲的傳教式精神,如果不是 阿育王 因為提倡《阿毗達摩》變造經典打破傳統缺口的影響,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近現代的學者指出,作為「大乘菩薩道」基礎的「慈悲觀」,極有可能是受到波斯盛行的「彌特拉」崇拜啟發,而且在「大乘經典」中,作為「大慈象徵」的「彌勒」和「大悲象徵」的「阿彌陀佛」,也有自波斯的「彌特拉」的朔源。
然也有人認為,由《奧義書》的傳統思想融合《克裏斯那》的崇拜,並吸取波斯文化因素而產生的《薄伽梵歌》對「大乘菩薩道」思想的影響更大一些。
《薄伽梵歌》攝取《奧義書》之精華,其主要內容的成立遠在於「大乘佛教」之前,「大乘菩薩道」重悲願、利他、入世的精神,與「原始佛家」專重解脫的理念完全不同,但不代表他們不注重入世,只是隨順「緣生法」而已,但卻與《薄伽梵歌》的立場完全一致,說明前者受後者的思想而來(幾年前,我曾見過有佛教徒將《薄伽梵歌》當做佛法在弘揚)。
《薄伽梵歌》的思想與「原始佛家」的思想完全不同,它的基本宗旨涅槃與世間,出世理想和入世精神的調和。這是因為,一方面《薄伽梵歌》繼承《奧義書》的思想,認為世界如幻如化、無常、生滅、不可得、不淨,故以舍離為修道準則,而另一方面,卻又在宣說,如來藏(梵)清淨寂滅,遍一切處,能建立世界萬法,世間諸法皆從真性而生,諸法有生滅,而此真如不生不滅。
因此,即不可貪著世間假相,但又不可違背真如能生萬法的道理,所以即入世又出世,力求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協調,修瑜伽者,必須以舍離與有為結合才能圓滿修行。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般若經》乃至大乘諸經中得到證實,它們宣導的就是,生死與涅槃不二,菩提與煩惱不二,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空有不二,凡聖不二,又宣導世出世間一切法當體即空,菩薩唯有證入此不二法門,方能成就無上菩提。簡單說這是模棱兩可的「唯心論調」,無論怎麼說都可以,怎麼掰都贏。
與此同時又極力的貶低「阿拉漢」為“自了漢”、“焦芽敗種”、“沒慈悲心”,只知“沉空守寂”,所以不能成就無上佛道,一切只因不知本具「常住真性」,清淨寂滅,且又能建立萬法(如《維摩詰經》,《楞嚴經》中甚至將「阿羅漢」貶成入魔),這就是「大乘經典」何以貶低「阿拉漢」的真正緣由。
而在「原始佛家」,解脫與煩惱,涅槃與生死是不可能融合的,釋迦牟尼 宣導的是修持「四聖諦十二因緣得明斷無明」(優婆底耶 充分闡明了「原始佛家」與《薄伽梵歌》的區別。
到了「部派佛教」時期,寺院生活依然與世俗隔離,故「大乘佛教」(菩薩道)的不住生死、不入涅槃的思想當然是不可能從「原始佛家」這樣的實踐中發展而來,更沒有其他資源,所以它必然是由「吠陀婆羅門」的《奧義書》及《薄伽梵歌》涅槃與世間調和的理想化,深刻的滲透進後期佛教的結果。
再者,「大乘菩薩」與慈悲相應的「平等性智」(證自他平等,諸法平等)也是從《奧義書》及《薄伽梵歌》演變而來。
第一,「原始佛家」提倡五戒中的不害不殺,完全是由經驗而來的,它著眼於一切生命都有樂生畏死的心理,而《薄伽梵歌》所提倡的慈悲則完全是形而上學的。而《奧義書》提倡的是:人必愛我,方能愛一切眾生,其宣揚的真我是一切眾生本具的。
在此基礎上,《薄伽梵歌》標榜「同體大悲」,謂真我平等、本具、不二、遍入一切眾生,故瑜伽行者視眾生之苦樂屬我、我所。
歌云:入彼瑜伽者,視一切有我,我亦有一切,故一切平等,這既是「大乘菩薩道」所宣導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來源。瑜伽行者出於自他平等之智,才有入世利他之大行,這與「原始佛家」所宣導的「緣生法」思想是那樣的格格不入。
第二,《薄伽梵歌》又從自他平等引申出苦樂平等,諸法平等,世出世間平等。其以為慈悲與暴戾,清淨與染汙,正直與邪惡,以及凡聖,苦樂等一切對立之相,皆從我(真如、如來藏)所出,皆以我為本體,故聖者平等視一切法。
歌云:世間眾生同一體,萬差千別自相同,視一切平等,乃真瑜伽士。這與「大乘菩薩道」觀一切眾生本具佛性,本具智慧德相,又觀諸法當體即空,同一空性的思想是完全的一致,而在「原始佛家」中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思想。
第三,與此相關,「不二平等」,作為菩薩深智的境界,也是來自於《奧義書》和《薄伽梵歌》。《奧義書》中提到,「心、物不二」,是認知的最高境界,主客對待是因為有二元對立,是有分別,心有分別,則仍有法執和無明,基於此,大乘經典中每每出現苛斥,貶低「阿拉漢」有分別心,法執未斷,正是緣於此。
《薄伽梵歌》則把「心、物不二」擴展為「諸法不二」,認為“有二”或“雙味”統攝一切虛妄分別,世間由此顯現出種種差別幻相,乃至出現貪欲與爭鬥,聖者得不二之智,等視一切,複歸於“一味”之自我。
如「大乘華嚴經」中所云:「奇哉,奇哉,大地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無明妄想而不能證得,若無無明妄想,則一切智,自然直,無師智自然顯現。」
另外,在大乘「真常系」的經典中隨處可以看到這樣「諸法不二平等」的內容,如「生死涅槃不二」,「菩提煩惱不二」,「世出世間不二」,「凡聖不二」等等,不勝枚舉,而這樣模棱兩可的矛盾內容,在「原始佛家」時期是完全不存在的。
還有,佛菩薩化身的觀念也印證了菩薩思想與《奧義書》和《薄伽梵歌》思想的關聯。「大乘佛教」認為,諸佛菩薩法身清淨寂滅,常住不壞,能出生一切功德,能隨緣建立妙用,所以能無量劫出現於世,廣度眾生,這實際上就是「婆羅門教毗濕奴神」化身的翻版。
它乃是緣於「巴克提運動」,尤其是「克裏斯那神」的崇拜。譬如,諸佛和觀世音菩薩有光焰之身,充滿虛空,每一個毛孔都包括一個他方世界,其中有無量無邊的菩薩和眾生,這與「克裏斯那」在「阿周那」面前顯現幻身,是出於同樣的思維模式。《薄伽梵歌》的影響也使「大乘佛教」通過佛菩薩實行的“外力拯救”得到發展。
另外,「大乘佛教」特有的「諸法如幻,心性本淨,如來藏本具」的觀念也正暗合了《奧義書》的思想,於此相關的還有以下事實。
1.最早的「菩薩眾」是成立於西元前二世紀末,印度西北部的“在家佛教信眾”,它的興起與《薄伽梵歌》的流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重疊的。
2.《薄伽梵歌》極力貶低出家修行,推崇讚歎在家持法,主張慈悲濟世,反對解脫煩惱斷輪回,以及強調「真俗不二,凡聖不二」,這都與居士佛教運動的精神完全一致。在此,可以明白為什麼在有些大乘的經典中,在家居士可以呵斥貶低出家眾,甚至是「阿拉漢」。
3.在家信眾團體由於獨立於僧團而存在,使包括《薄伽梵》崇拜在內的宗教思想滲入佛教更加的方便。因而可以肯定,《薄伽梵歌》是通過在家信眾團體逐漸滲入佛教之中,最終導致了「菩薩道」的產生。
【三.信仰主義的強化與大乘佛教的產生】
信仰主義的強化也是促使「大乘佛教」產生的重要因素。在「大乘佛教」中,有著不少禮拜十方諸佛,祈求加被和懺悔罪業的經典,而這些內容則與《奧義書》的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
「原始佛法」本來重自證,而不重信仰,如《雜阿含》卷21:「尼犍若提子語質多羅長者言:汝信沙門瞿曇得無覺悟觀三昧耶?質多羅長者答言:我不以信故來......我已常住此三昧,有如是智,何用信世尊為。」
而在大乘的經典中,如《阿閦佛國經》、《大阿彌陀經》、《無量壽經》等主張通過信仰往生淨土,《般舟三昧經》等主張通過念佛得三昧,現在諸佛悉立於前,佛教在這裏變成了真正信仰意義的“宗教”了。這種巨大的思想轉變,必定是印度本土原生宗教思想不斷影響下的必然結果。
再說,這種「強化信仰的佛教」產生,與希臘波斯的文化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一世紀,希臘人、塞種人、貴霜人等相繼入侵印度,使印度西北成為本土文化與波斯、希臘等文化交融的場所。
當時留存的佛教藝術(文學作品)反映出希臘、波斯文化的影響是極深刻而顯著的。因此,佛教的思想受後者的影響也是自然的,但這主要應當通過思想的比較來證明。
就大乘「淨土宗」的信仰而言,它的波斯文化的因素是很明顯,前面說過,「阿彌陀佛」或「無量光佛」的信仰既是從波斯宗教信仰演變而來。波斯古經《阿吠斯塔》描述西方有極樂世界,名曰「無量光」。「大日如來」、「阿閦佛」的形象也反映了波斯、希臘對「太陽神」崇拜的影響。
另外,「大乘佛教」中的菩薩,如觀音、地藏、文殊普賢等,是人類抽象原理的演化(慈悲、願力、智慧、實踐的化身),這與「吠陀信仰」中的「自然神」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而更像「所羅亞斯德教」、「猶太教」中的天使,這意味著他們的形象源自外來宗教和印度本土信仰的糅合、薰染下被創造出來的。
其次,佛教的信仰運動可能更多的是從本土的「巴克提教」中汲取營養。「巴克提教」是南印度民間信仰與《奧義書》(吠檀多)思想融合的產物。換句話說,印度教本身的信仰化乃是《奧義書》中本有信仰與異端信仰融合下的結果。
《奧義書》中早就提到了通過虔誠的信仰,持咒達到禪定的方法,也相信通過虔誠的皈依,可以得到神的加持,從而獲得覺悟和解脫,另外還以信仰願力決定往生「梵地淨土」,若人臨終前一心願入於「梵」,則死後必入「梵界」。從中,確實可以看出「大乘淨土宗」的思想重視願力、信仰、他力的慈悲。
印度的「巴克提教」,尤其是對「薄伽梵」的崇拜,就是將《奧義書》的思想整合並吸取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巴克提者,為虔誠信仰、崇拜、獻身、摯愛等意。虔誠信仰出於對神殊勝存在的信任。
《薄伽梵歌》認為「薄伽梵」是至上的「我」,是「萬物之源」,是「無生無滅」,「恒常清淨」,「究竟圓滿」的。修道者以虔誠「信仰自我」者為最高,依吠陀、祭祀、苦行、佈施皆不能見「薄伽梵」實相,唯有依虔誠的信仰,與世尊的大悲願力,才能如實見之。親證「梵我」者,若在臨死前發大誓願,死後,定入清淨的「梵界」,最終與「真如」、「梵」融為一體。
將這種思想與佛教對比,可以確定以下幾點:
第一,它的淨土信仰在理論上有著明顯的家族相似性,「淨土佛教」對佛,淨土的描述與《薄伽梵歌》對「至上神」,「梵界」的描述是一樣的。
「阿彌陀佛」信仰,是依據「阿彌陀佛」的誓願力,任何人只要具足信願行,臨終一定會得到祂的接引,往生至祂的清淨佛國,這實際上與「巴克提教」的拯救是一樣的。由於《薄伽梵歌》的形成遠在「大乘佛教」之前,故設想後者沿襲了前者的思想也是很自然的。
第二,「大乘佛教」的佛菩薩系統也與《薄伽梵歌》的神話有著顯著的親緣性。佛菩薩化現世間說法度生,只是「毗濕奴神」化身的翻版。「觀音菩薩」的形象與「毗濕奴」和「克裏希那」及印度本土信仰崇拜有關,「文殊」和「普賢」的形象則脫胎自「梵天」與「帝釋」。
「過去七佛」對應於「吠陀」中的「七仙」,佛的三身分別與《薄伽梵歌》的「無德梵」、「有德梵」、「化身梵」對應。《觀音德藏經》說「本際佛」依禪定生「觀自在」,後者與眾神創造世界,這與「毗濕奴」通過苦行創造「生主」和「梵天」,後者再創造世界,遵循著同一思維模式。
與「毗濕奴」一樣,「如來」不僅是神,而且是“創造菩薩”,眾生的神中之神。可見,「大乘佛教」的“有神論”可溯源自「巴克提教」思想。
另外,作為「淨土思想」起源之一的佛塔崇拜,正是以「在家信眾」為主體,其產生也與「巴克提運動」造成的濃厚的信仰主義氣氛有關。
【四.大乘佛教觀點的定型和最終走向】
「原始佛家」本來是經驗和自然主義的立場,其宗旨是通過客觀世界對主觀世界的影響,強調「我空法有」身體感官世界的暫有,而在暫有中的交互影響與不斷變化的規律恒在。
但「大乘佛教」所謂的真如、空性、法性、實相、勝義、法身、不二、絕對、佛性、涅槃、寂滅等,都提示著「我空法空」,另外在「形而上」再次建立極樂淨土則絕對存在。通過否定現實經驗的來詮顯形上的絕對,這在「原始佛家」中是絕對沒有的,這樣的思想完全是《奧義書》的思路。
大多數學者認為,大乘的真如、如來藏、佛性、第一義諦、空性 等等與《奧義書》中「梵」的概念有著本質的相同。如印度已故總統政治家兼教授的「拉達克利須南」和「杜特」學者等都認為大乘的「如來藏」、「真如」乃是“世界永恆”的本體,與《奧義書》中的「大梵」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事實的確如此。
所以大家不能說這是「大乘菩薩道」或「印度諸教」把現實世界說成假的,再建構一個假的能滿足所有的虛幻世界又說成是真實的,因為這種宗教概念必須迎合人類在現實世界遭遇不滿後又幻想著在某種次元空間加倍得到的心靈需求。另外在「大乘菩薩道」這種概念又稱為「真空妙有」,這也是「唯心論」或「自由心證」的最高境界。
綜上所述,「大乘佛教」的產生,主要是印度這個國度的人民百姓對神的極度依賴,加上「吠陀婆羅門教」和「種姓輪回制度」才是印度「雅利安人」三千多年來種下的異常鞏固的大根,即便是佛教曾經盛極一時。
所以在「核心思維」被扭曲的「部派佛教」之後,「婆羅門」的「奧義薄伽梵」等「大乘思想」借著沙門之間的自由改教和交流,逐漸一步步的對「部派佛教」滲透,進而影響導致的趨勢和結果。
這種滲透使「大乘佛教」確立了形而上學的絕對,但「大乘佛教」在隨後的發展中,逐漸從「空」向「有」的立場傾斜,最後在「如來藏佛教」中,絕對被明確為「至上我」,於是,「佛教」完全被《吠檀多》思想同化(宗教化),而這一點,也奠定了中國漢傳佛教的根本走向。
28/08/2020 龍爺改編。